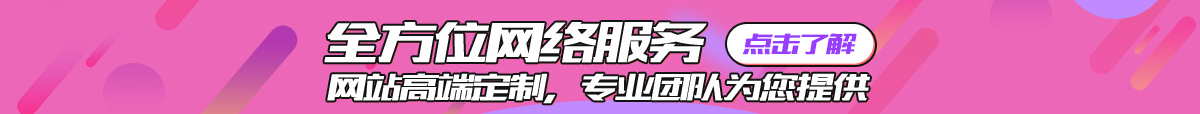第二十七章 十七岁 难行之路
他淌著血泪而微睁的双眼,是不是正注视著她呢?
她抓著他的肩膀轻轻地晃著,不停呼唤他的名字,他却没半点反应。
他僵硬的唇为何没能开口告诉她「别怕」呢?前一刻不是还温柔地对她说,她是他挥刀的理由?怎麼转眼间他变得像个木头癫痫抽搐怎么办呢似的什麼也不说了?
当她意识到他掌心的温度渐趋冰冷,她的思绪也逐地陷入罪恶的流沙。
他,一动也不动。
那些被夜风吹落一地的余烬,好似她眼角的泪珠不知该往何处流,原地打转。山谷的风为何比她先哭出声?被烧得焦黑的枝梢弯著腰在哀悼什麼?
她垂首将耳朵贴上他的心口,听见心跳声微弱得有如风中残烛。
为什麼事情会变成这样?
她伏在他的胸膛上,压抑著想哭的情绪,小手揪著他染血的衣领而颤抖,她勉力挤出一丝微笑,告诉自己这没什麼好哭,他不过是睡著罢了,但她的嘴角很快地又沉了下来。
因为,任她抓得再牢,也阻止不了他那逐渐流逝的体温。
她咬著下唇,心口痛得令她难以言喻,想说些什麼唤醒他,却再说不出一个字。
拜托你醒来、别吓我了、不要丢下我、我们一起离开好吗……
他听不见了,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她呆愣愣地看著他,心头像挂著块秤坨,让她难以呼吸。想哭,却无法,深怕只要她一哭,他就真的会离她而去。
她将双手挡著自己的眼杭州癫痫医院哪个比较好眶,不让泪掉下来,但那些泪珠却仍不如意地溢出眼角,她紧紧阖上双眼,想著这或许能让她流的泪少一点。
一闭上眼,那些撕心裂肺的痛楚却随黑暗袭来。
这一切不都是她造成的麼?
她若是没选择参加那场宴会,会使他受伤而疏远她?
她若没轻易答应凯伦的邀约,会害他承受那麼多风险与自责?
她若没任性地吻了他,会使他背负著罪恶而离开?
她若能勇敢地告诉她父亲这一切都是凯伦与诡术妖姬的阴谋,事情会演变至此?
她若能在他出现的当下勇敢地跟著他离开,会害他负伤应战吗?
是她害了他。
自认为一切的抉择都是对的,殊不知那只是自欺欺人罢了。打从她决定为了变强而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,便是一场错误赌局的开始。看似美艳的外貌只是掩盖自己内心丑陋的藉口,华而不实;看似坚强的意志实则一昧逃避的虚伪武装,脆而不坚。
太多的泪水蒙蔽了她的视线。
连自己很重视的人都保护不了,还谈何保护*子民这种重责大任?连自己想要的是什麼都不知道,又如何能做出正确的抉择?
思及此,她便再也无法欺骗自己到底做了多少害人害己的事。这些日子她到底在做什麼?她到底做了什麼让自己变强的事情?她终究只是个拖油瓶不是吗?看著一地的死尸,看著他失去意识前的绝望眼神,她,到底保护了谁?
她以为自己总是勇敢地面对残酷的命运,她坚信她这样的做法正确而无误,直到她听见奎因喊她「公主」时,她竟发现自己的内心像被狠狠地挖了一块肉似的,痛到令她快要窒息,那一瞬间脑门也像是被那两个字给贯穿一样,什麼话也说不出来,她一点都不想承认,她就是对方所说的「公主」。
「为父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」
她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?想起父亲在亡母坟前对她所说的话,无限的罪恶感再度紧缠著她心脏,痛,原来悔恨的痛,远比茫然无知的悲伤还要重上千百倍。
看似坚强的抉择,只不过都是一次又一次懦弱的妥协而已。
她真的有顺著自己的意志去做过抉择麼?不,那些决定,统统都只是循著自己的脆弱、胆小、恐惧、犹豫、无知而懵然做出的逃避行为罢了。
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,一味地躲在被子里颤抖著不肯出来。
任眼泪模糊了视线、沉浸在自己所构筑的悲惨世界中自怨自艾。
无论她睁开双眼几次,梦魇仍都纠缠著她不堪一击的心,渐渐地,她都快分不清了,分不清何谓梦境与现实,而这竟顺理成章地成为她逃避一切的藉口。
她到底在害怕什麼?
她很害怕的,不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麼?
那麼,她所做的一切,到底有何意义?
她竟然害自己很爱的人,倒在血泊中一动也不动地任生命流逝。
「泰隆……」
她的指甲崁进自己双臂,烙下一道道的爪痕。
「……对不起。」只可惜再多的懊悔也唤不醒他了。
睁开双眼,她发现他的面色比刚才还苍白许多,她紧蹙著眉,手臂上的爪痕溢出滴滴血红,但,还不够痛,这远远不及他所受的苦痛的万分之一啊!
她茫然地站了起来,森林寂静得毫无生气,月光探出云层,撒在他毫无血色的面容上,也照亮那条通往德玛西亚的山间小路,但她的灰色双眸却披著层层的阴霾。
她垂下双眼,陷入沉默,面无表情地沉思著。
眼前那看似笔直的道路,实际上却是一个十字路口。
她若往前,便再也无法回头,她将成为敌国的公主,一生一世面对那位她不爱的男人,而泰隆也势必会被德玛西亚人处决。
她若回到诺克萨斯,那些排山倒海的舆论将会压得杜.克卡奥家族喘不过气,而她的父亲也必定会一刀斩开泰隆的项上人头。
她若驻足不前,他会死,他将会再一次残酷地在她眼前离她而去,而且永远不再回来,一想到那样的结局,不,她根本无法接受那样的结果,他若真的死了,也是被她害死的,她绝不允许这样的自己继续活下去!
她紧咬下唇,转身看向毫无声息的他,双手用力地扯开裙角的衣料,将一缕缕的白布撕下,含著泪,将他身上的伤口一一裹住。
「我不准你再离开我……不准……」
她深吸一口气,使尽娇小身躯的全力将他沉重的身子拉了起来,并拾起那条染血的围巾将他的臂膀固定在自己的肩上,那一瞬间他的重量险些将她给压倒,她咬牙,强迫自己纤细的双臂撑起他高大的躯体。
她将脚上的高跟鞋踢开,裸著脚,踏出了艰辛的一步,尽管她根本不知道她能扛著他走多远,也不知道究竟能去哪里,但此刻的她,坚信自己还有很后一条路。
一条很崎岖难行的道路。
既不能前进,也无法回头,更不可能驻足不前,只得去寻找一个未知而渺茫的希望。
他的身躯好重好重,她还走不到几步身子便紧绷地颤抖著,她逞强地打直身子前进,却一个不稳狼狈地跌倒,她顾不得膝盖被石子刺伤的疼痛,泛著泪,再度吃力地将他扛了起来。
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……」她不准自己哭出声。
再也不想无助地流著泪,眼睁睁地看自己所爱的人消失在眼前。
再也不想让无形的枷锁困住自己的思路,她只想不顾一切地与他远走高飞。
这是很后一次机会,错过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已经失去太多太多。
她扛著他前进,步伐蹒跚而缓慢,不是往前,也并非往后,而是进入了周边的森林之内。她心里清楚,发生了这种事情,过不了多久,不论是诺克萨斯或是德玛西亚都会派人过来查看,走在大路上一定会被发现。
她踩著焦黑的落叶,赤裸的脚底被烫得她快哭出来,但尽管路再难行,她也不能允许自己一错再错了,比起失郑州治疗癫痫病很*的医院在哪去他,那些皮肉的痛楚又算得了什麼?
愈是深入森林,月光就愈是稀薄,眼前的歧路愈来愈黑暗,一股股恐惧袭上心头,每踏出一步都深怕踩到毒蛇,每走过一棵树木,就担心树上会有什麼饥饿的野兽。
她颤抖地停下了脚步,理智不断被恐惧拉扯著。她从未面临这样的危机,不论是眼前的一片黑暗,还是她背上濒死的泰隆、脚底的灼伤,抑或是那很根本也很严肃的问题,他们究竟能去哪里?她不知道,也不去想,若真要去想,不就又被困在那无形的牢笼之中了吗?
她地低喃著他的名字,小手覆上他冰冷的脸庞,再一次确认她是如此不想失去他,随后,一个坚毅的眼神浮现,她抽出泰隆的钢刀,那把刀又重又长,她吃力地举著钢刀使劲劈开前方刺人的枝叶,同时也借力使力,使她前进的步伐少了点艰辛,多了些力量。
一步、一刀。
疲累的四肢阻挡不了她前进的意志,尽管脚底的伤口沾著泥土而发疼、尖锐的林叶不断地划伤她细致的肌肤、他的重量压得她快无法走动,但她还是顶著一颗不屈不饶的心,迈著颤抖的双脚,步向未知的崎岖难行之路。
她,已不愿再妥协。
山林的另一头,薄雾徘徊林间,林荫顶端交错的枝影透下稀微的晨光,泥土铺满湿滑的落叶。一位女子赤裸著身子独自步著,凡她所经之处,踏过的叶子皆烧了起来,随著她的步伐越走越远,一道长长的焦黑足迹拖曳在她身后。
她浅蓝色的皮肤生著些许的龙鳞,浑身散发著烫人的热气,覆肩的散乱红发与浏海挡住她流著泪的双眼,但那些泪珠还未流下脸颊就被蒸发了。
她缓缓地走著,穿越林荫,步入一座湖泊。
踏入湖泊的同时激起了漫天的水蒸气,她让自己沉入了水中,越走越远,越沉越深,水中的她没有一丝挣扎,放任自己沉入黑暗的渊流,仰望著湖面的波光,她平静地闭上眼。
倏地,一股强大的力道将她由水中拉了起来。她咳咳地看著视线中模糊的人影,对方紧紧揪著她的手臂不放,不让她继续往下沉。
「为什麼要这麼做?」
那人厚重的嗓音开口这样问。
她虚弱的面容透著一丝愧疚:「属下没有辩驳的理由。」湿透的红发贴著她的脸颊,身子持续散发著滚烫的热度,四周弥漫著她与河水激出的水蒸气。
「你明白那不过是一场戏。」他扶住她的肩膀,深邃的双眼炯炯有神。
「请别这样看我。」她低著头,说话的语气有些颤抖。
「我要你明白。」
「殿下,你不该在这的。」她撇过头,刻意不正视他的双眼。
「希瓦娜。」他唤著她名字的语气没有因她的冷淡而有所动摇,接著说:「这对我们而言都是痛苦的。」
她阖上酪黄的双眸,微微皱著眉。想起她自从得知了他要迎娶卡西奥佩娅的那一瞬间,身上的龙鳞便开始不受控制地发热,起初她以为自己可以慢慢缓下心中的怒火,但她很快就发现,她愈是想抑制,形体的变化就愈加失控。
情况一发不可收拾,她明白自己若不去做些什麼事来阻止这种情形,她很快就会变成一头不受控制的圣龙。
她摇摇头。那是不被允许的情感。
「我以为你明白我的苦衷。」他的厚掌拨开掩盖她双眼的发丝。
她忍著眼眶中的泪水,身上的鳞片愈加突出,由颈脉之处延伸至左脸,覆盖住一半的脸庞,表皮的温度也愈发炙热。
「殿下,我无法再控制自己。」半人半龙的脸愧疚地说著,泛著火光的鳞片正逐渐往右侵蚀。
「……杀了我。」
顷刻,他不顾被烫伤的风险将她拥入怀里,两人伫立在水中,弥漫四处的白色蒸气将他们隔绝度外,她愣愣地靠著他的胸膛,说不出话。
「我,嘉文四世,背负著守护德玛西亚的重责大任。」
他凝视著她的双眼,语气不带半分犹豫。「我若让你死去,还谈何保护*?」
她伸出那遍布鳞片与尖锐指甲的双手,紧紧地环抱著他,在他的背部划下一道道焦黑爪痕,哀伤地说:「我……无法原谅我自己。」
「我说过。」他将她的脸捧起,让她看著自己的双眼。
「你的罪就是我的罪,而你的未来也就是我的未来。」
她咬著下唇,他的字字句句都敲击著她脆弱的心,也支撑著她的意志。
忆起当时嘉文不顾一切也要拯救她被圣龙族追杀的命运之时,他们携手完成那艰钜的挑战。他带领他的部下歼灭了圣龙一族,战况惨烈,整个部队只剩下他与两名士兵,当她挥动巨大的龙翼,载著身受重伤的他离开圣龙窟的一片火海时,她问他为何愿意牺牲一切也要救她,只见他毫不犹豫地说:
「为了德玛西亚的正义。」
他时常挂在嘴边的「正义」,让他做出的任何事情都显得合理。
她不懂什麼正义,她甚至不懂他为什麼要将她半人半龙的罪孽视为己任,但她只懂一件事--「她的命是他救来的,而她将以一辈子的忠诚来偿还这份恩情。」
只是,究竟她的忠诚是出於他口中所谓「德玛西亚的理想」,还是对於「嘉文四世」本人呢?
「希瓦娜。」他唤著她的名,她愕然地醒过神来。
「是我辜负了你。」
「殿下,请不要……」她其实不清楚他的意思。
「我答应你,会用更好的方式,完成我们的理想。」
她睁大双眼盯著他,说不出话,只感到脸上的炽热感好像逐渐消退。嘉文露出微笑,继续说道:「绝不会是伤害你的方式。」
她颔首,原本还散著火光的燐燐之肤一瞬间降成人类的体温,她感到一阵晕眩,失去了力气,嘉文温柔地接住了倒下的她。
「对不起,希瓦娜。」
他抱著她离开了湖泊,闭起黑得深邃的双眸。
「连心爱的人都守护不了,谈何保护*子民呢?」
他微微一笑,暗自希望她没听见他无意间说出的话。
再崎岖难行的路,也有他为她披荆斩棘。
不知走了多久,密林顶端的黑夜竟已转为灰蒙蒙的晨色。
她累得再也走不了,双脚瘫软跪地不听使唤,红色围巾一松,她背上的泰隆也摔到了地上,她吃力地移动双手爬向他,伏在他胸膛听著他微弱的心跳。她握著他冰冷的手,强迫自己别去想那些不好的事。
好累……累得无法思考……
四周浓雾渐起,好不容易见到一点光线,却又被雾气给团团遮蔽,比起黑暗带来的未知恐惧,能见度不到两公尺的浓雾更让她感到不安,明明看得见,却得更加担心雾里有什麼未知的危险。
好累……累得想闭上眼睛……
她发现自从她倒下的那瞬间,身体累积已久的疲累竟一次席卷而来,她已经无法再用意志力去驱动早已疲惫不堪的身体了,现在,她大概只剩撑开眼皮的力气而已。
「如果我睡了,你大概也不会醒来了。」她视线模模糊糊,不再是泪水的关系,而是用尽一切的力气换来的沉重倦意。
也许……是累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……
「我们会不会,一起死呢?」她的眼眶不再是想哭的红泽,而是乌青的倦痕。
忽地,她看见浓雾中走来一道人影。
那人有尖锐的翼状斗篷,手持一把十字弩缓缓走来。
「是她吗……」她看著眼前的人影,深知她再也没有方法能保护泰隆了。
那人举起十字弩朝向他们,她听见了箭矢上膛的声响,只能缓慢地闭上眼。
「咻--!」
一发箭矢迅速地穿越了他们,打中了他们身后不远处的树干上,她听见一声尖锐的鸦鸣响彻林间,随后也听见振翅的声响,听见那只鸟仓皇飞离现场的拍翅声。
「为何会有如此浓重成年人癫痫病如何治疗的黑暗气息跟著你们?」她开口了,嗓音听来是相当低沉的女声。
她愣愣的,没有回话,而那人也逐渐步向他们,现出了她的面貌。
「那只乌鸦,是什麼?」她稍微移开暗色的墨镜,露出黑色的眼珠看著她。
「乌、乌鸦?」
那人瞄了一眼他们的情况,眼光立刻被倒在地上的泰隆给吸引住。
「哎,怎麼是你?」她无奈地笑了。
(未完待续)